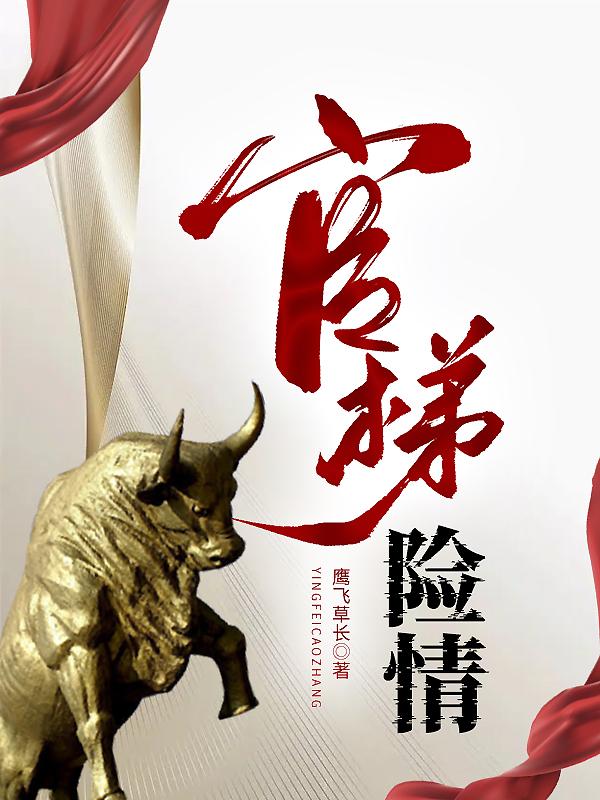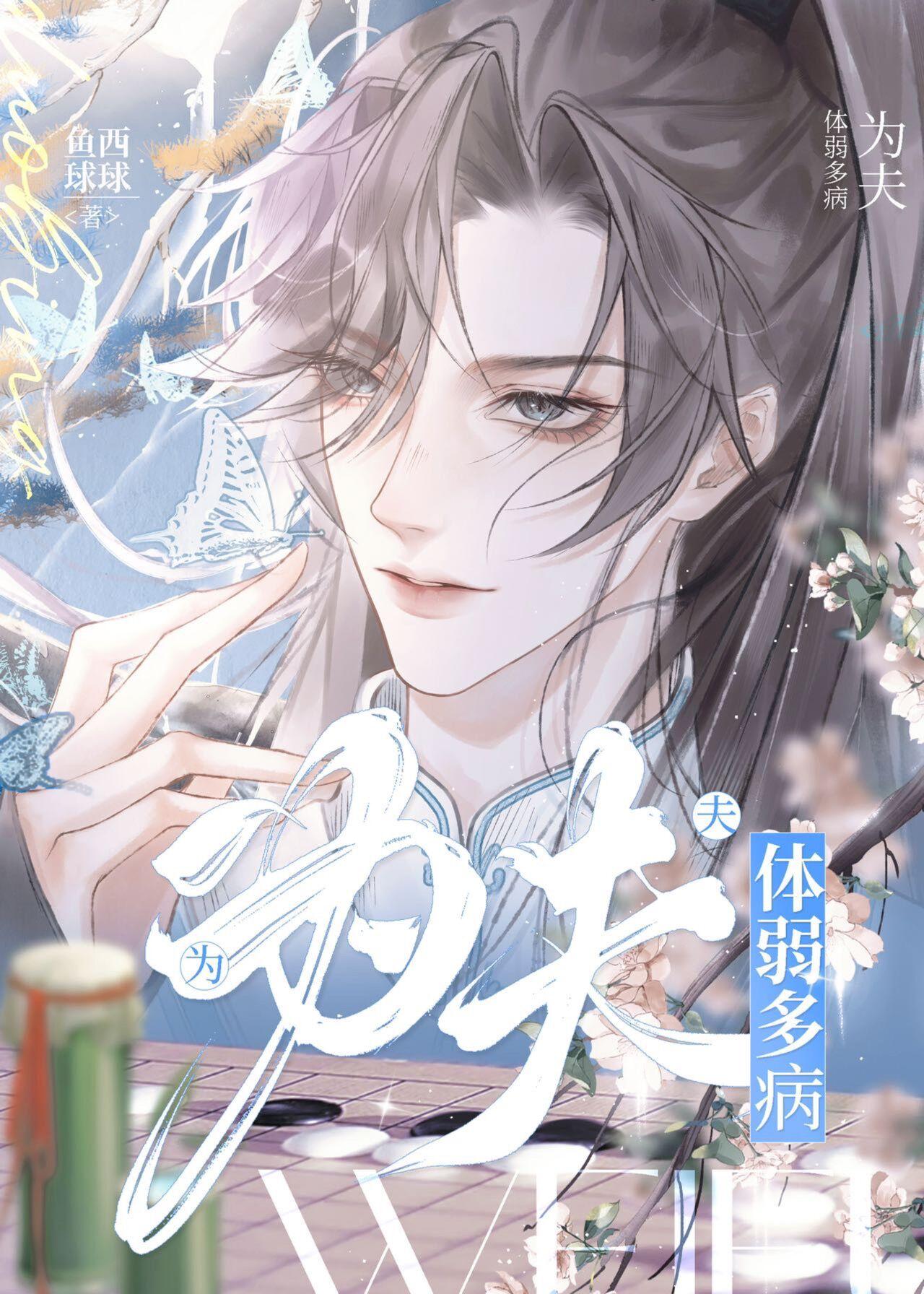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野心炽爱by臣年 > 第73章(第3页)
第73章(第3页)
“这串数字,明明白白写着按人头收税。”
我话锋一转,连翻数页,按图索骥,语意犀利而轻佻。
“可是贺县均摊之时,又以田亩算之。岂不是,收了两笔?”
萧庭之怔然,良久回神,破口大骂。
“好呀,这个纰漏,如此破绽,我却浑然不知经年,我真是,上了年纪不中用!”
我却微微笑着,并不责怪。
“这空子虽显目,却铺了好大一块遮羞布,量是大人年轻气盛,火眼金睛,也未必能察觉。"
萧庭之眼底一丝错愕一闪而过,继而目露羞愧之色,虚心讨教。
“那么苏大人以为,这是用了甚么障眼法呢?”
我略一颔首,徒出长篇大论。
“其一,运笔炉火纯青,必有高人指点。不出意外,是个老练的刀笔吏。”
我眼珠微不可察地一转,辗转瞬息,笑叹依旧。
“春秋笔法,久仰大名。虽言之不适,却斟酌不出更好的词句。”
我手指轻捻起研磨候在一旁几乎要干墨的毛笔,圈出了帐册上的一句缘由。
“其言道,马车所过之途,山路崎岖,所损不计其数。运至周县,辖官大怒,因而降罪于民,苛捐杂税加重,民众苦不堪言,两地民怨鼎沸,渐成水火不容之势。”
萧庭之细细听去,却一头雾水,见我但笑不语,意味深长,额角淌汗。
“苏大人,下官……下官听不出玄机所在,还望大人点破。”
我意料之中地一抬眉梢,语重心长道。
“难怪,难怪。”
见俯首之人眉关加深,苦不堪言却不敢轻言,我使他如愿以偿。
“你与吴大人被调到此地做官,绝非偶然。”
这次我没有再卖云里雾里藏着掖着的关子,开门见山道。
“你与吴大人都是登科进士出身,一心只读圣贤书。熟习四书五经,殿试上口若悬河,书卷上斐然成章,正经儒生。苏某,记错否?”
得到两人震惊而敬重的注视后,我这才不紧不慢地接上。
“想必二位也晓得,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相对培养的,还有另一支群体,名为,刀笔吏。”
话题兜兜转转,落回之前见首不见尾的伏笔上。我语气如登高台,悲切而沾染风寒。
“正是拿捏了你们不通咬文嚼字,玩弄字句的认死理劲儿,把你们凑一对,真可谓是一叶障目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