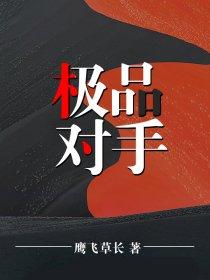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我在洪荒当武祖免费观看 > 第11章 难道你真把诸葛亮当补药吃了(第1页)
第11章 难道你真把诸葛亮当补药吃了(第1页)
洪武年间,京城的皇宫内,朱元璋依旧稳坐于龙椅之后,专注地批阅着大臣呈上的奏章。他的朱笔在纸页上游走,或点或书,偶有几篇需要反复查阅,他会回头再找寻旧折对比。而与他对峙的,则是久未入宫的毛骧,这位锦衣卫的统领虽在外人面前总是从容自若,但此刻站在天子面前,却总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。这种情绪每次来访都会浮现,仿佛每踏进一次宫门,就受到一次惊吓。然而职责所在,他又不得不来。片刻后,朱元璋放下奏章,随意瞥了眼立于对面的毛骧,问道:“县试结束了吗?”毛骧听命垂首,谨慎作答:“回禀圣上,县试已按期完成。”“没有出什么岔子吧?民间可有动荡?”听到这里,毛骧稍作迟疑,随即回道:“回圣上,县试期间并无异常,只是考生起初对试题颇有微词,不过目前情况已好转,无需担忧。”朱元璋听罢,目光微凝,眉宇间带了几分不悦,低沉地说:“详细说说。”“是。”毛骧依言开口,将事情原委条理分明地陈述出来:“此事源于您钦点的本届恩科主考官胡惟庸。”“胡大人履职以来,并未另作他举,只依照惯例行事,唯独在命题时,在卷末添了一道策论题。”“考试结束后,许多考生觉得此题过于艰深,不知从何下手,因而心生不满。”“但胡大人此举并非针对特定个人,大家议论一番后也就平息了。”“因整个过程未造成大的乱,且迅速得以解决,锦衣卫并未紧急上报,还请圣上见谅。”毛骧语气坦诚,既未夸大事实,也未隐瞒细节,完整地将事情报告清楚,还为下属作了合理解释。对于锦衣卫来说,这种程度的监视毫无难度,整件事情就像发生在他们眼前一样清晰,所以毛骧才能汇报得如此详尽。朱元璋听罢,眉头越皱越紧,竟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一件玉如意摩挲起来。许久,他才缓缓开口:“所有考生都在埋怨胡惟庸出的题目太难吗?”“正是如此,陛下!”“啧……胡惟庸到底想干什么?这可是乡试,他为何要出这么难的题?而且,是什么题目能让咱们大明的所有考生都开始抱怨了?”仿佛是在发问,又像是自言自语般感叹了一阵后,朱元璋突然下令道:“宋利,你去一趟,把乡试试卷拿来让我看看!”“遵命,圣上!”平日里一声不吭的宋利,在朱元璋身边总是如一抹淡淡的影子。但只要皇帝有所吩咐,他便能立刻有所反应。宋利悄无声息地退下,只留下朱元璋独自沉思。不多时,朱元璋用手中的玉如意轻轻敲击桌面,转向毛骧问道:“毛骧,这期间可有人试图平息考生的不满?”这一次,毛骧没有立刻作答,而是沉思片刻后才慎重回答:“据我所知,没有!”“一方面,锦衣卫所有人确实未曾发现这样的迹象;另一方面,此事牵涉到今年大明所有参与恩科考试的考生,我不相信有人能同时让这么多人闭口。”朱元璋听完微微点头,表示默认。之后,大殿再度归于寂静。毛骧额头冒汗,总觉得今天自己明明没做错事,却一直忐忑不安。好在就在此时,救星宋利捧着一张巨大的试卷快步而入。总算得救了!毛骧长舒一口气,接过试卷,目光刚扫到最后一页,朱元璋就愣住了。“这是什么?”“宋利,你是不是拿错了?”宋利苦笑着弯腰回禀:“回禀圣上,我在礼部调取试卷时也以为拿错了,特意核查过了!”朱元璋震惊地看着试卷末尾那个格外显眼的“0”,无语地撇了撇嘴。这是什么东西?我完全看不懂啊。想到这里,朱元璋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,干脆转头吩咐道。“宋利,去一趟胡惟庸府邸,让他马上进宫!”“咱们倒要听听,这家伙是怎么搞出这么个东西的!”“既然天下读书人弄不清楚,咱们这些不识字的更是琢磨不透,那就让出题的这个家伙给我们讲清楚!”------------胡府。“胡大人,圣上有旨,请您即刻入宫觐见!”传旨内侍的话音刚落,胡惟庸略显疑惑地眨了眨眼。不过他并未多想,依旧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,甚至连衣服都没换,仍旧穿着这身家居便服。上了马车后,他双手揣在袖子里,悠哉悠哉地朝记忆中的皇宫驶去。在前生的记忆里,这样的宫廷之行时常会发生。所以,他对这次入宫其实挺淡然的。毕竟现在他早已是闲散之人,既无心思翻什么身,也没有做过什么招致非议的事情,朱元璋应该不至于专门针对自己。因此,这是他穿越以来首次进宫,内心反而充满好奇。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,后面更精彩!的确,心态平和之后,他对朱元璋充满了兴趣。毕竟,这位可是开国皇帝,上下五千年来罕见的草根逆袭者。虽然前世与朱元璋有过不少面对面的交谈,但那终究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,总像是隔着一层纱。现如今亲历其中,也算是实现了夙愿。不久后,马车缓缓停在皇宫门口,随行的内侍先行下去为胡惟庸领路。有内侍带路,再加上胡惟庸的脸,进入皇宫简直易如反掌。毕竟几个月前,这位还经常在这儿“上班”呢。和守卫们熟络地打了个招呼,胡惟庸背着手沐浴着春风,从容不迫地在宫中漫步。他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四处打量、观察。他对这一切感到新奇。皇宫,尤其是住着人的皇宫,谁能不感兴趣呢?毕竟后世那些仿古建筑,不过是缩小版的应天府皇宫罢了。现在走在真正的皇宫里,不就得多看看?可惜时间有限,路途总有尽头,在小内侍紧张得满头大汗的指引下,胡惟庸终于踏入御书房的大门。“臣胡惟庸拜见陛下。”“免礼,赐座。”身为前丞相、现翰林学士的胡惟庸,既是朱元璋创业初期的旧臣,地位自不可与毛骧这样的内廷仆从同日而语。宋利刚搬来凳子,他便毫不客气地坐下,坦然自若地望着朱元璋。比起记忆中的模样,眼前的朱元璋似乎更显疲惫。每日堆积如山的事务,各种烦忧接踵而至,无疑也在折磨着他。或许是前尘往事的影响,还没等朱元璋开口,胡惟庸已先感慨道:“陛下,请务必保重身体,这些时日不见,您消瘦不少。”此言一出,满室皆惊,朱元璋亦抬眼凝视胡惟庸,目光中满是意外。四目相对,朱元璋只在那双清澈的眼眸中读到关切与坦然。想到对方的身份,朱元璋心中一暖,紧绷的脸庞也不由自主地松弛下来。“唉,朕事务繁忙,不像你这般自在。你这一病,倒是把差事推得一干二净!”“如今看来,你恢复得不错,气色比朕强多了。”胡惟庸当场被戳穿在家悠闲度日的事实,但他毫不尴尬,反而眉梢一扬笑道:“圣上忘了吗?当年在红巾军时,我就说过,这辈子注定要享福的!”“这段日子大难不死,我觉得啊,今后还是安安稳稳、舒舒服服过日子为妙!”“您麾下人才济济,让我闭门闲居,岂非美事一件!”一句“圣上”差点让朱元璋情绪失控。对啊,眼前这位昔日丞相虽然保养得宜,看起来还像个年轻人,但实际也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功臣。再想想当初这家伙就爱偷懒,果然没变。想到往昔沙场征战的岁月,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愈发温和,嘴角的笑容也愈加明显。“行了,朕知道你:()大明:我在洪武当咸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