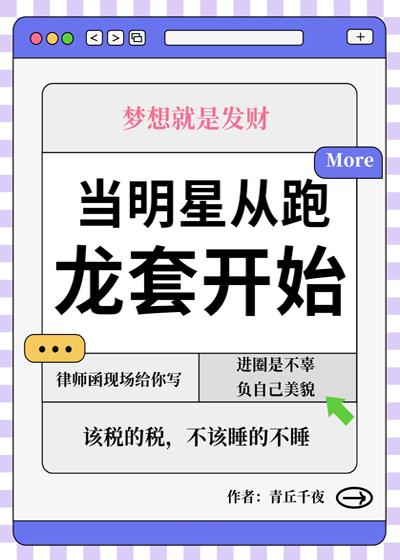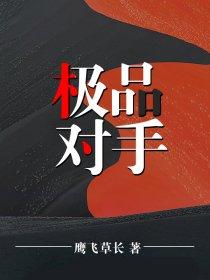EXO小说网>写到书签上面的句子 > 九 信号与沉默(第2页)
九 信号与沉默(第2页)
“都……有。”她故作神秘地说了一句。
“哟,了不得啊。”王瑛子眯着眼看她,“真是个大作家,每次旅行都变成一次采风。人家旅行是散心,你出门旅行就是去掘金。”
刘奕羲低头笑了笑,不否认,也不多解释。
王瑛子瞥了她一眼,忍不住感叹:“我要是你读者,我现在一定在你微博底下嚷嚷:你到底写的灵感是哪一个——是意大利的天空,还是天空底下的哪个人?”
刘奕羲笑着摇了摇头,没说话。
但那一刻,她脑海中掠过的,确实不是罗马的某个建筑,而是某个在音乐厅中沉默的背影——被舞台灯光拉长,在她心里留下的形状,至今都还未淡去。
另一头,祁祺刚在公司落座,电话会议便准时接入。
对面是他即将合作的新剧导演——业内以叙事精细、节奏严谨著称的一位人物。两人此前虽有接触,但这是第一次就项目做正式沟通。
通话比预期顺利得多。导演语气简洁、条理分明,提出的角色定位与整体风格,与祁祺对剧本的阅读感受出奇一致。
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,人物复杂、背景扎实,对角色的层次把控要求极高。但也正是这样,才吸引了祁祺。
通话尾声,导演确认了试装与定妆拍摄的窗口期,进组时间也随之敲定。
“正式开拍前会有两周左右的打磨期,”导演说,“先做角色分析和小组读本,后续进入封闭排练——文戏优先处理,武戏和长镜头穿插技测。”
“明白。”祁祺简短地回应。
这通电话一结束,整个剧组的执行团队也迅速展开工作。
祁祺的个人档期被锁定,工作室同步收到剧组的初步拍摄计划:试装时间、造型会议、对戏排期、体能调整、定妆照、技测时间线,还有项目签保密协议、配合宣传窗口期的内容梳理。
从这一刻起,他正式进入角色前置阶段。
熟悉的节奏。有些忙碌,有些沉静,像把身体和意识一点点收拢,等待新一轮的“入戏”。
会议一结束,祁祺从会议室里出来,没往休息区走,而是径直转向了电梯。
助理艾伦正准备跟进剧组发来的时间表,见状连忙追上去:“哥,你去哪儿?”
“补电话卡。”祁祺头也不回地说。
“啊?”艾伦愣了一下,“不是说今天晚上……”
“现在。”祁祺语气平稳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节奏感,“越快越好。”
艾伦一边小跑跟上,一边翻手机查最近的营业厅,嘴里嘀咕:“上次你手机掉那儿都不知道,我还以为你真的不着急……”
祁祺没回应。
但他的脑子里,从早上飞机落地到现在,一直在回放一个画面:她写下的那两句话,那枚书签的质地,她合上笔记本前轻轻侧头的样子。
他从没想过,自己会这样惦记一个人。
不是因为外形,不是因为情境,而是她安静得像某一页纸,却又在无声里留下痕迹,让他回到现实后,还清晰记得——她的眼神,是带着字句质感的。
他甚至还记得她说话时语气的起伏、目光的停顿,还有那一瞬间的轻笑。
祁祺垂下眼,手指下意识地摩挲着衣兜里的笔。那是他从书里取出后放进去的,像一块怀念的凭据,又像一个等待回应的提示。
他想找到她。
至少,要打通那个号码,听听她的声音,哪怕只是说一句:
——“我看见你留给我的了。”
营业厅人不多,流程也快。
不到二十分钟,祁祺就补好了电话卡,恢复了原号。服务员刚把手机递过来,他便迫不及待地点开短信界面。——空的。
没有任何新消息。
祁祺站在原地,拇指轻轻划着屏幕,眉头微微拧起。
当时他只给了自己的号码,只留了一句话:“你打给我,我告诉你想知道的。”
可她没有打。